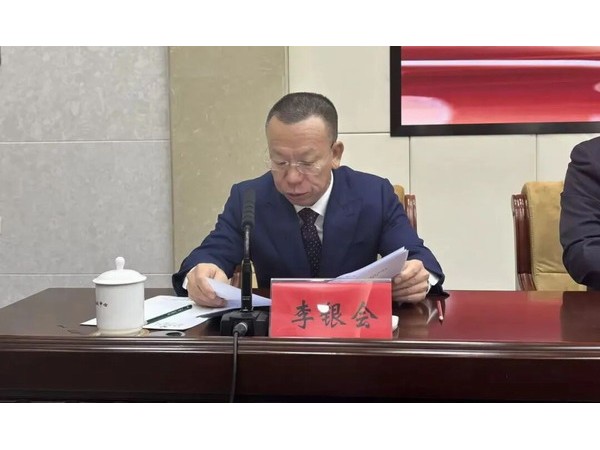近年来,“废话梗”成为各大网络平台上一个频繁出现的无法忽略的文化现象。在“微博”“百度贴吧”等平台上,我们时常可以看到下面这样的回复:“咱就是说就是说;我直呼我直呼;我上次看到这番话的时候还是上次;你搁这儿搁这儿呢;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简言之,通过表意内容和表意方式的单纯重复,言说者将整个句子变成了一句空洞的废话。在相当多的场合下,“废话梗”不仅没有传达任何交流信息,甚至与所回复的内容都无甚关联。熟练运用“废话梗”的往往是同时使用多个网络平台的青年人,他们自如地在不同平台之间将各类只言片语进行重复、变化、引申,从而炮制出一连串“废话”。因此,“废话梗”不仅是当今网络上的流行文化现象,也从侧面标记出当代青年人的交流形态和特征。
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论者试图从“废话”的构成机制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此进行解释,也有论者从这种语言现象中看到了年轻人对于主流话语和“父辈”的微观反抗,更有论者从文学和美学的角度将“废话”的主题追溯到一些经典作家的论述(如朱自清关于“废话”的讨论),甚至发明出“废话文学”的范畴来煞有介事地为这一现象定性。「1」不过,在进行这些深刻的讨论之前,我们或许需要首先考察一个非常浅显的问题:“废话梗”出现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下,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总是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废话”,那么为什么“废话”会演变为“废话梗”的显著现象?既然“废话梗”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网络文化现象,而始终和其他现象——如“凡尔赛文学”——并行不悖,那么,从“废话”这一语言现象的性质乃至本质入手讨论问题,会不会从根本上搞错了提问的方向?
从技术和媒体形态的发展而言,这里所谓的当下语境,无疑包括近年来自媒体的迅猛发展、短视频的兴起和流行,也包括从“网络直播”和“虚拟主播”到“直播带货”等一系列改变传统媒体与受众的互动方式和交流模式的技术运用和创新。与此同时,近年来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日常生活中接收信息的方式和通信方式的变化,都使上述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在质和量上都截然不同于互联网技术方兴未艾时的状况:二三十年前网络技术的初步发展和应用,在伦理上曾向人们提出过“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野问题,事实上,这一在当时被视为棘手的问题反而从侧面表明,所谓“虚拟世界”在当时仍然停留于某种对于“现实世界”的增补阶段,以至于两者相对清晰的边界可以在伦理和文化上得到评判(所以才会症候性地出现“网瘾”这样的词)。而正如所有二元对立的构造最终都会通往对立项的相互影响、渗透和污染,在新媒体时代,网络所代表的“虚拟世界”早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行为模式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作理所当然的“网络神话”之一——一个人可以在网络上“扮演”和他本人截然相反的人格和形象,他可以过一种与自己在现实中的社会身份截然不同的生活——早已不可能了:这不是因为越来越多网络平台的后台要求用户进行实名认证,而是因为人们所谓的“现实”生活已经不可避免地与网络牵连在一起。网络已然是形塑人们日常生活的必不可少的一环。
当然,上述大背景本身无法解释“废话梗”的产生及其再生产。但它提供了包括“废话梗”在内的网络“梗”文化得以生长的条件——简单来说,“梗”文化在根本上涉及和回应的问题是:当网络的普及将彼此间差异极大的,即处于不同地域、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们如何进行交流?为了具体地阐释“废话梗”的意义(如果它有“意义”的话),笔者建议将这一现象和同时期流行的另一个“梗”放在一起讨论,即一个同样可以在各大网络讨论平台见到的回复:“演的吧?”而随后其他人的跟帖回复,往往会像对暗号一般,用不同语言将“演的吧?”这句“梗”在原初语境下引起的相应回复变了花样地进行复制。我们要问的是:在人们乐此不疲地再生产这种内容空洞甚至毫无意义的“梗”的时候,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首先,毫无疑问,作为网络文化或亚文化的显著表现之一,所谓“玩梗”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例如,在“网瘾”和“电子游戏”一样被视作洪水猛兽的时期,即时通信软件 QQ(旧称 OICQ)上的人们,就习惯于用诸如“886”“你是 GG 还是 MM”等表述进行交流——不足为奇的是,当时传统媒体对于这类表述的批判,在之后的历史时期中也以同样的方式得到反复,无论对象是所谓“火星文”还是如今青少年间流行的拼音首字母缩写。而不管是“886”还是“废话梗”,这些乍看起来意味不明的符号起到的一个共通作用是,就像相互对暗号一般,使言说者能够确认彼此间共享着同一种交流前提。于是,能否领会这些符号并做出相应的恰当反应,在青年人那里就成为区分“我们”与“他们”——无论这里的对立意味着“虚拟世界 / 现实世界”“真 / 假”“新/旧”“年轻人 / 老年人”“时髦 / 过气”“离经叛道 / 墨守成规”,还是其他——的重要标志。
在“废话梗”这里,言说者同样可以通过对“废话”的使用而确认彼此之间交流的默认前提,时刻确认自己与对方的“可交流性”。但更重要的或许是“废话梗”与以往流行的“梗”之间的差异。在我看来,这里的差异涉及两个层面,概括起来即“交流形式”的层面和“交流内容”的层面。而在分期的意义上,这两个层面也分别在“网络梗”演化的三个阶段中呈现出不同面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无法也无力给出明确的、关于“梗”种类演变的历史时期划分,而只能以不同阶段较为典型的事例来推进讨论。并且,尽管我在这里使用了“阶段”的概念,但不同种类的“梗”往往会同时流行。这一现象也符合笔者曾经尝试讨论的社会的“气泡化”状况。「2」就第一阶段来说,让我们仍然以早年 QQ 上的表述为例予以说明。众所周知,“886”是对“bye bye 了”的谐音表达;类似地,“GG”对应“哥哥”,“MM”对应“妹妹”。相似的表述还有“PLMM(漂亮妹妹)”——是否可以说,如今青少年之间流行的拼音首字母缩写的交流方式,其实是一种“返祖现象”?不难发现,这些表面上看来显得新颖的符号,其实不过是对既有的一些固定表述的局部翻译或改写;这些符号的使用者有意通过它们来突显“我们”与“他们”的不同,但事实上,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在这个时期不仅都意识到并恪守着所谓“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边界,而且根本上只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着通常意义上的交流——即人格性的、话题相关的、相对完整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使用“886”等“时髦”的表达方式来标新立异的行为,就像所有试图离经叛道的叛逆少年的行为那样,仍然遵循着他们所试图反叛的交流规则和社会关系。更要命的是,这些被广泛使用的符号,其中有不少正是由平台本身提供的,以至于用户们所做的其实是通过习得一套既定的标识系统来完成一些他们不依靠这个系统也能实现的交流。在这一阶段,网络上用户的互动平台主要呈现为论坛、聊天室等,这些以交流内容为主的平台自然要求人们保持日常生活中交流的法则和模式,因而“梗”往往是边缘性,甚至是点缀性的——不仅“废话梗”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废话”本身也受到严格的约束:“灌水”(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严禁灌水”)这一如今已经很少人使用的说法,就再好不过地反映了当时网络交流的基本特征。于是,青年人一方面急于通过标新立异来强调自己与上一辈在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乃至价值观上的差异,另一方面他们最终又不得不意识到,能够为那些他们用于强调自身“新颖性”和“独特性”的表达方式提供支撑的,似乎就只有单纯的代际差异。(在这一点上,一个再好不过的“症候”便是 2000 年左右出现的“80 后”一词。)
然而,这些单义的、意义明确的符号,不久就被一些看上去不明所以的“梗”代替。尤其是进入 2010 年代后,随着各大社区平台的发展,随着“聊天室”淡出人们视野、“论坛”逐渐被“微博”和“贴吧”等平台取代,网上出现了一众无法被直接“翻译”回日常语言、无法明确解释其含义,甚至无法明确其用途的表述,其中典型的包括“奥利给”“皮皮虾,我们走”等。如果说“886”等早期网络表述仅仅是在日常交流之上加了一层时髦的外观,那么当年轻人频繁地、闹剧般地在留言区或讨论区打出“奥利给”的时候,我们显然无法简单地把这些表述“还原”为某种习惯性的日常说法。非常重要的是,比起“886”“GG”“MM”等符号,“奥利给”是一个明确的引用:言说者明白无误地提醒人们,他在引用一个“梗”。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说,言说者通过这一引用行为而有所指:虽然“奥利给”本身的意思并不明确,但并非什么内容都可以被贴上“奥利给”的标签。换句话说,如果“886”充分体现了言说者的人格性——因为他想说的正是“再见”——那么在“奥利给”的引用这里,言说者的人格性变得相对模糊,却也并非完全不可见。至少可以说,言说者借助引用表达了某种特定的情绪。并且,相比于“奥利给”这个较为极端的事例,还是有不少“梗”在表达着较为明确的意义内容(如“你知道得太多了”),使人可以从中辨认言说者的位置和态度。笔者将此视为当代媒体语境下“网络梗”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一方面,许多可视作与“886”发挥类似表意功能的表述得以产生;另一方面,更多意义暧昧、用法模糊的表述得到广泛流通,使人们对它们的使用很难再被简单翻译回“日常语言”。“梗”更多地从中性表述的领域向言说者的主观情绪方面倾斜。(回想一下官方媒体对于“给力”的追认式使用,同时却没有类似地对于“奥利给”的使用,就不难看到这里微妙但重要的区别。)青年人不再需要通过向他们的“上一辈”大喊“我是新的!”来标识自己的新颖性,因为网络的普及已经自然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区分于恪守“虚拟世界 / 现实世界”之分野的“上一辈”人。
第三个阶段——我将“废话梗”视为其中一个代表性事例——有别于以上两种类型的“梗”,可以说“废话梗”完全抹去了言说者的人格性,也抹去了明确的情绪性指向:从语言形式层面来说,“废话梗”通过单纯的重复,违背了日常交流的基本预期;同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从表意内容的层面来说,“废话梗”不仅掏空了任何实质性的交流信息,而且它指向的往往是原本已经作为“梗”而流通的其他表述,因而无所谓某句“废话梗”究竟表达了“愤怒”还是“感动”。例如,“你搁这儿××呢”原先就已经作为一个得以广泛传播的“梗”句式而存在,但如果仅仅是在特定场合为它填充内容,那么这一表达就仍然处在上述第二阶段。只有当被填充的内容本身变得空洞,整句话变成“你搁这儿搁这儿呢”的时候,“废话梗”才得以产生:在这里,“可交流性”被保留下来的同时,交流的内容和交流者的人格性完全付诸阙如——这是一种不交流的交流,一种自始至终不向对方展露自己的“交流”。就算有人想要刨根问底地追究这句话的“意义”,他也只能被带到原先的“梗”那里。在“梗”作为一种“引用”的意义上,“废话梗”始终是一次二次引用。可以想见,有不少人在使用“废话梗”的时候并不知道它所依据的原初的“梗”及其语境——后者的特殊意义和情绪,也并不是“废话梗”的言说者所关心的。因此,哪怕原来的“梗”的确表现了某种情绪,它在经过二次引用后也丧失了这一表达功能。换言之,在形式和内容上,“废话梗”同时实现了自我空洞化。在这个意义上,相较于在网络上“创造”另一个自我人格(或“主体”,如果你喜欢)的“神话”,如今人们在运用“废话梗”的过程中恰恰试图通过隐蔽自身而彼此确认最低限度的社会性。(所以,比起“废话梗”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迄今居然仍然有论者试图从“人格性神话”的角度分析“废话梗”现象。)于是,有意思的是,相较于依靠关键词触发来进行留言回复的机器程序,在任何内容下面都回复“演的吧?”的人们无疑看起来更加接近机械;但与此同时,毋庸置疑,运用“废话梗”的人们从中感受到的愉悦,并不来自“说废话”这一行为本身,而是来自别人用同样的“废话梗”予以回应的时刻——就此而言,一些从“废话”的心理机制和语言功能入手的研究,恐怕一开始就搞错了方向。这里,“废话梗”也将自己区别于以往的“梗”的运用:“886”也罢,“奥利给”也罢,它们在被写下的时刻,使用者就已经完成了自足的表达;这些表述并不规定某种特定的回应。与此相对,几乎像是机械性的触发机制一样,一句“废话梗”始终预期着另一句“废话梗”的回应。
初看起来,这一尝试自我隐匿的现象似乎和新媒体时代格格不入——毕竟,不仅在“快手”和“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上,每天都有无数的普通用户在无偿地向平台提供自身的劳动(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只求获得更多人的关注。一方面,如今无论在哪个网络平台,“流量经济”所占据的优先地位,似乎时刻要求用户对任何话题的讨论都以过度参与的方式——在这方面最具概括性的一个说法当数“带节奏”——进行自我展现乃至自我表演,无论其具体的呈现方式是“微博”上的骂战、“bilibili”上的弹幕,还是直播间里的礼物刷屏,更不用说“微博”“知乎”等平台上那些鼓励用户积极发言的奖励机制了。用一个显得陈旧的术语,似乎新媒体时代前所未有地要求和催促人们表达自身的“主体性”,要求每个人的人格性在场。另一方面,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趋势是:这些平台向用户要求和期待的“自我表达”,并不是以往“博客”时代那样的网络版日记,不是一种冗长而复杂的、具有内心深度的自我叙事,而是一个表情、一个动作、一种瞬间的反应,甚至是无法被确定为某种特定“情绪”的反应。简言之,人们借助新媒体所表达的,是某种当下的、瞬时的、前反思性的“情动”,而不是某种完整的“自我”形象。「3」强调这些“情动”并非自然存在的、有待被凝结为“情绪”的东西,而是被新媒体技术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恐怕也已经是批评理论分析下的老生常谈。这些无法被轻易归类、概括和整理的“情动”式表达,并不呈现言说者或行为者的人格性;同样,运用“废话梗”并从他人的“废话梗”式的回应中感到愉悦的人们,恰恰是在这种前反思的、非人格性的甚至是机械性或动物性的“瞬间”中,找到与他人的片刻“共情”。与此同时,面对充斥于网络的“情动”性表达,以及其中包含的种种暴力、非理性、戾气,“废话梗”作为一种保护性的交流机制,能够使人在实现基本的社会性需求的同时得以全身而退。从这一角度看,“废话梗”看起来颇像是厌倦了“内卷”、选择了“躺平”的青年人的犬儒式的语言表达。
自不待言,“废话梗”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网络平台上的大部分交流都在采取这种形式;毋宁说,这始终是一个局部性的现象,一个甚至难以被“前景化”的现象。在一些人津津乐道于“说废话”的同时,也有另一些人(或同一批人在另一些场合)操弄着例如“yyds”“破防了”等衍生自游戏领域的、具有相对明确内容指向的表述。「4」正因如此,“废话梗”的流行表明,面对日趋分化和细化的网络文化生态,任何从 19 世纪西方现代的主体观念出发的观测角度——如表达个性、彰显人格性、追求关于他人和社会的完整叙事等——所产生的貌似宏大的分析和论述,都只是某个特定圈层的特定话语的自我再生产而已。
重要的是,如果说“废话梗”的交流让诸多言说者既可以在“情动”的意义上实现某种“共情”,同时又允许他们从交流过程中抽离自身的人格性存在,那么我们也许恰恰可以从“废话梗”的流通中发现某种新颖的集体性。换言之,面对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情势与其在网络上的再现,“废话梗”或许寓言性地提示我们注意任何一种政治或文化话语内部、任何一个严肃或不严肃的表达底下的“情动”维度。不同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对于集体性和公共性的想象,也不同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笔下作为“共同体”之想象的文化条件,呈现于网络平台上的这种“情动”式的集体性既不以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及其意志为前提,也不通往某种群体性的政治意识;不如说,这总是一种非人格性的集体性,乃至一种非公共的公共性。当这种公共性不包含个人的主体性介入,甚至不必预设个人的社会身份的时候,既有的政治哲学概念——如“交往理性”“交叠共识”等——在此或许都不敷用了。重复一遍:正是当代网络平台所创造的交流的即时性、简短性、流动性,使基于“情动”式反应的“共情”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量生成并同时得到呈现,这一点并不以每个言说者的主观意愿为转移。这种独特而新颖的集体性或公共性,几乎是言说者在私人意义上“玩梗”或对内容进行消费时的副产品,因而它显然无法凝聚也无法承载某种明确的、概念上稳定的“集体意识”,甚至很难在一般意义上要求某个人来为他不经意间留下的一句“演的吧?”承担“责任”;但这种集体性或公共性,确乎比每个个体的“意识”更直观、更直接,也更真实地反映着这些言说者与他们的生活之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而这些言说者自己甚至也无法用意识性的语言来表达(articulate)这种关系。换言之,这种非公共的公共性所透露的是,迄今为止为论者们所默认的“私人 / 公共”的对立结构,已经在根本意义上被颠倒了:论者往往会以选举、议会、集会等集体性的活动为典型,强调民众通过自觉的意志行为参与政治的“公共性”;相对于这种可见的“公共性”,“私人性”指向的则是不可见的、可被还原为有限的个人生活的维度。但在新媒体时代,一方面,由于网络对于人们生活本身的形塑作用,原本是不可见的“私人性”,如今不仅通过众多共情的瞬间变得可见,而且总是呈现出复数性、共情式的在场;另一方面,在“气泡化”的社会和网络生态下,所谓的“公共性”因让位于不同圈层的特殊表达而变得愈发“不可见”。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者首先应该做的,与其说是强行分辨哪种特殊表达才是真正的“集体意识”,不如说是正视并应对“情动”式的共情所呈露的非公共的公共性。
不过,与此同时,需要警惕的是:假如像日本思想家东浩纪多年前在《一般意志 2.0》中所描绘的那样,「5」期待网络上呈现的这些“情动”可以直接以非政治或前政治的方式参与和影响实际政治,那么我们收获的恐怕也只有一堆针对政治议题所做出的“情动”式反应,而后者的另一个名称即“仇恨言论”。因此,如何对总是已经以集体性或复数性的形式存在着的、“情动”式的共情进行连接,如何对它们进行疏通和引导(而不是从内容上做出审美或价值判断),以及如何应对既有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工具在面对这些现象时的失灵问题,应当成为我们阅读当今网络文化时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展开的工作。当然,这一工作不可能简单地为“废话梗”赋予所谓的积极意义;毋宁说,既然“废话梗”所透露的非公共的公共性最终与言说者的生活、与他们无法积极地自我表达的生活现实密切相关,那么所有的疏通和引导也都必须与这种现实密切相关。例如,如今许多通过短视频甚或“鬼畜”视频的形式来对一系列当下性的,涉及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的事件进行整理和创作的行为,或许可以被读解为回应乃至疏导上述非公共的公共性的一项令人瞩目的手段。也就是说,在触及具体的“内容”的同时(甚或在此之前——在标题的层面上),事实上它们首先试图唤起受众在“情动”层面上的反应。相比于传统媒体(包括博客和网络新闻客户端)的再现方式,这些创作更直接地与现实发生关联,因为它们所诉诸的“情动”的节奏和速度,恰恰符合现实中事件发生的节奏和速度。同时,这一不可忽视的现象也提醒我们:这些新媒体时代出现的新颖的创作行为,早已不能被还原为某种自足的“作品”,甚至也不是后结构主义者津津乐道的“文本”:因为非常明显的是,这些创作与它们诉诸和唤起的反应,无法被简单归类为同一层级的“叙事”——与其说两者之间形成了“互文”,不如说这些创作更像是某种带有叙事外观的“容器”,它们试图凝聚、呈现和引导集体性的“情动”式反应。事实上,在一些近期的创作中,“废话梗”也如其所是地被创作者积极加以重新引用,以达成讽刺、幽默、调侃或批判等不同效果。重复一遍:这些效果并不来自“废话梗”的文字表面(例如,“咱就是说就是说”这句话本身无所谓讽刺还是批判),而是来自这些创作者在对“废话梗”的重新引用的过程中,对总是已经存在于“废话梗”底下的众多“情动”所做出的回应。
因此,在更大的意义上,我们也未尝不可以将这些创作理解为一种迈向新的动员方式的实践:尽管我们在这里很难辨认出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动员所包含并要求的人格性、个体性、相对明确的集体意识等要素,但通过“情动”式的共情而汇聚在这些新媒体的创作形式下的集体性,的的确确产生着无法忽视的社会性力量。这些力量同样会反过来形塑我们的现实——被网络覆盖的、动态的、技术性的、多层次的、由不同话语和势力相互交织和冲突的现实。像如今许多自发的短视频创作者所做的那样,将青年人不经意间运用的、使用后便弃置一旁的“废话梗”和其他许多表达加以重新引用和转化,从而为非公共的公共性赋予一种相对明确和稳定的外观的行为,也许恰恰是在召唤和预期着一种将来的集体性,以及一种新的践行共同生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