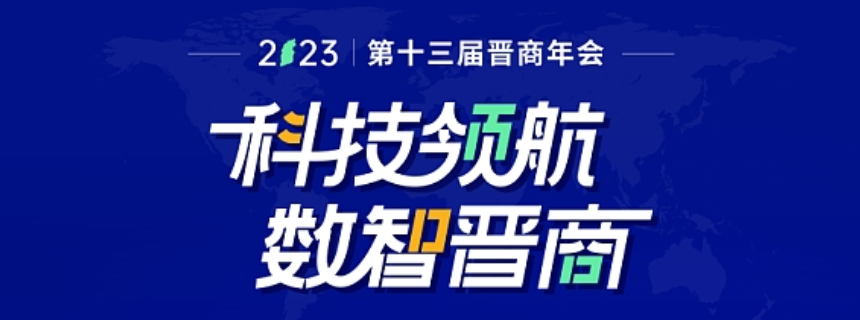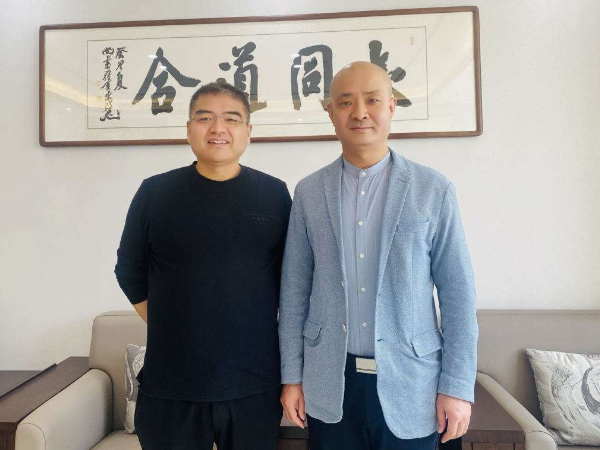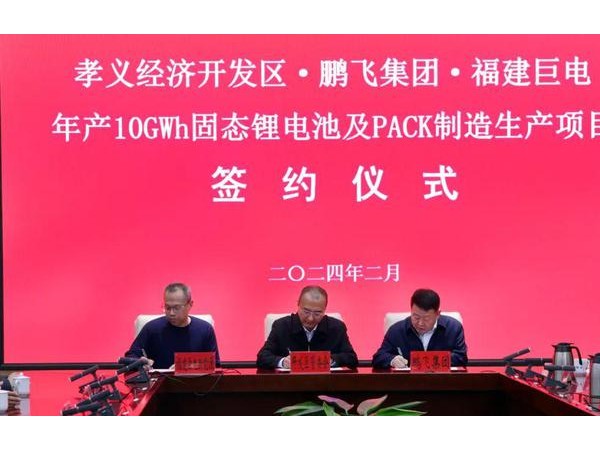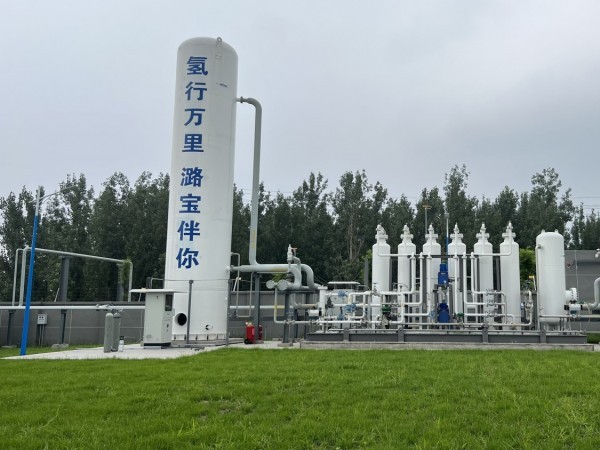“我说过,我不会放弃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这不是一句话,是一种思想,是历史责任。”
“再提笔写小说有什么感觉?我跟你讲,像流水一样的快乐。”
身高1米92、穿46码鞋的“大冯”,坐在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会客室里,说起重回“虚构”的快乐。屋子里,汉代的陶俑、北齐的摩崖拓片、唐代的菩萨像、宋代的天神像、明代的文官像、清代的彩绘屏风,还有民间的银冠、布老虎和昔日山西豪门的上马石,这些年从各地收集来的艺术品,被他安插进各个角落,“颜色、位置稍微有一点不舒服都不行,非得把它摆好看了”。
墙上挂着一幅作家莫言题写的打油诗:“大冯如巨树,每见必仰望。做人真性情,交友热心肠。赤脚追天马,空手擒野狼。明知山有虎,三碗敢过岗。”
如“巨树”的冯骥才,近20年一直投身于文化遗产保护,唯有在路上,才能过把“小说瘾”。“从天津去河南,坐汽车八九个小时,一上车,闭上眼就开始想小说。有时想到一个情节,特别绝,可没法用笔记下来;有时正想着,司机说:‘冯老师,咱们到了啊。’一下车,又开始调查抢救了,那些故事和人物就像烟一样涣散了。”
去年9月,冯骥才到张掖开会。下午,年轻人都跑去马蹄寺玩儿,他就留在旅馆里休息,靠在床头上看新闻时,小说的开头突然冒了出来。他拿起手边的iPad,一口气写下去,直到学生们回来敲门,一看,已经三千来字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去西宁的高铁上写,回北京的飞机上写,回来接着写。
“突然这地方就开闸了,水就出来了。”
01、辫子、小脚与望远镜
这就是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
故事发生在1900年的天津城,裕光纸店的二少爷欧阳觉和法兰西军官的女儿莎娜,展开了一段离奇的爱情故事。但在那个动荡的庚子年,中西之间的隔阂、冲撞与屠戮碾压了一切,也将他们推入惨烈荒唐的绝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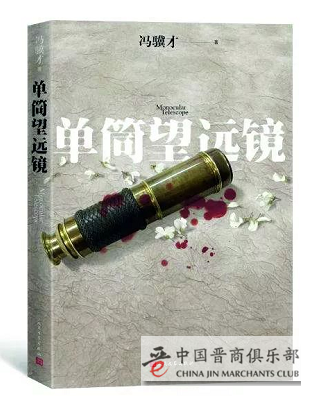
△冯骥才新作: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
只用50天,冯骥才便把初稿写完了。但在此之前,是长达30年的积淀与酝酿。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高歌猛进的现代化拉开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序幕,在中西文化的参照与碰撞中,很多作家开始转向自己背靠的乡土中国,寻找和反思“文化的根”。汪曾祺的江苏高邮,贾平凹的陕南商州,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的地域版图上一时热闹纷繁。
冯骥才的乡土,自然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天津。清末民初的天津,从两次鸦片战争、戊戌变法到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近代史上一连串的历史事件,无不与之紧密相关;1862年被辟为通商口岸后,九国租界先后开辟,工商业蓬勃发展,又使这座城市成为东方/西方、传统/现代彼此遭遇的舞台。
冯骥才的“怪世奇谈”系列,写的就是这一历史时空下的“闲杂人和希奇事”:第一部《神鞭》写于1984年,以天津城西挑担卖炸豆腐的“傻二”为主角,他凭借头上那根粗黑油亮的辫子,将估衣街上的大混星子、津门武林的祖师爷和紫竹林里的东洋武士一一击败,却被洋枪的一颗子弹将发辫打断。“我们每个人脑袋后边,都拖着这样一根沉重的、发馊的辫子,受其所累却不自觉。中国要开放、要前进,我们就要将它割除,剪断中国人的劣根性。”冯骥才说,“1985年《神鞭》被改编成电影,在天津大学的求是学堂放映后,学生们要我上台讲几句,我走到台边,说了这一段话。”
一年后的《三寸金莲》中,为了铺写“金莲文化”的繁琐、密集与刻毒,冯骥才参考各种文献,找小脚老太太们聊天,寻找各种缠足器物。小说中,他用几百字把缠足的全过程——从这个脚趾到那个脚趾再绕过脚面而后返上脚背等等,不加一个标点地写出来,“这就是中国文化令人窒息的自我束缚力,它在束缚你的同时,又用一种畸形的美将你征服”。
到了1988年的《阴阳八卦》,黄氏一家为寻找祖传的金匣子,婶侄反目,主仆决裂,挖地三尺,神医老道高人你来我往,却把家财散尽。兜兜转转、神神鬼鬼中,写出中国封建文化封闭系统的神秘与荒诞。
20年后,《单筒望远镜》作为这一系列的最后一部,仍接续着文化反思的主题。“望远镜是单筒的,是一只眼的视野,不是用两只眼睛把你看全。”这就暗示了在中西之间,各自存在着视野的偏狭——义和团的拳民们烧教堂、杀洋人,以所谓的“符纸”和“神功”与现代的枪炮弹药血肉相拼,固然有其愚昧和残暴;八国联军的殖民主义暴行,却给古老中国留下更深重的创伤。
小说中,冯骥才设置了庄婌贤与莎娜这一对人物,前者是欧阳觉的妻子,儒家文化的淑女,贤惠温婉,在八国联军屠城时不堪凌辱,自尽身亡;后者是他的情人,西方文化的产儿,自由率真,被义和团关进站笼,遭受百般侮辱。“我眼前出现了很多画面,一想到就流泪了。我不忍下笔,不忍让读者面对这样惨烈的景象。”
02、艺术家的生活
“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唯美主义者,说实话,我一向写不了太残忍的东西。”
冯骥才从小的梦是艺术,16岁开始学画,后来在书画社从事古画临摹,习马远、夏圭这一路北宋画法。
“文革”十年,冯骥才和妻子顾同昭一共搬了6次家,从五大道的小洋楼到8平方米的小屋,“不管在任何地方都让美成为胜利者”。夏天,他们在院子里种上丝瓜葫芦,支起棚架,体会一下瓜棚豆架的味道。三九天,外檐垂挂着一尺长的冰挂,西北风一吹发出声响,被他们称作“排箫”。玻璃罐子里养了两条小金鱼,白天上班时熄了炉火,下班回来水就冻实了,小鱼被冻在冰块中间,一动不动还瞪大眼惊奇地张望。
当时的老家具店里,抄家后的艺术品不时会在那里冒头,一幅印象派风景只要5块钱,一块汉瓦当一块钱,尽管经济拮据,他们有时也会咬牙买下一件特别眼馋的,摆在家里格外珍惜。从抄家废墟里捡来的书,封面早被扯去,冯骥才就从旧衣服上取下几块布,为《浮士德》《高老头》《呼啸山庄》装上书衣,尽量做得可意漂亮。
“文革”中有闲,冯骥才开始重新临摹《清明上河图》,用火柴吹灭后的余烬烧去锋毫的虚尖,摹仿张择端的秃锋。1972年,基辛格访华,随访的大使夫人包柏漪(美籍华裔女作家,代表作《春月》)来天津看望姑妈,听说楼上住着一位画家,好奇来拜访,看到画了半卷的《清明上河图》,竟跪倒在画前。冯骥才大惊,如遇知音,脱口而出:“我给你画一幅吧!”此后一年零三个月,他天天白日上班,夜里临摹,嚼着馒头咸菜,直至深夜。1978年,包柏漪将画带回美国,冯骥才觉得怅然若失。他手边留有一幅未完成的临摹卷,如今静静地躺在他的大树画馆里。

△冯骥才未完成的《清明上河图》临摹卷,如今静静地躺在他的大树画馆里。
从会客室出来,沿着楼梯上四楼,转角遇到一只汉代石狮,抬眼又看见一尊明代雷公,就到了大树画馆的门口。东汉年间,冯氏家族有一位冯异将军,为刘秀平定关中,却不求利禄功名。每遇众人争功,便避于大树之下,人称“大树将军”。冯骥才喜欢先祖的这个名号,便拿来为自己的画馆命名。
生于天津、长于天津的冯骥才,实际上祖籍浙江宁波。《单筒望远镜》里那位从宁波慈溪来天津开纸店,每天坐在厅堂里看槐树影满地的欧阳老爷,就是照着他的祖父来写的。
世人印象中,一提天津人,好像就是横着走路的混混儿、做小买卖的市井油子和成群成伙的老少爷们。而在冯骥才的记忆里,儿时的世界是曹禺《雷雨》里描绘的生活场景。他翻看作家陈丹燕的畅销书《上海的风花雪月》,从洋房、咖啡馆、夜总会到溜冰场,洋货店、手摇电唱机,感觉就像自己老祖母的往事那样息息相通。
“现在回想也很奇怪,当时明明住在租界的洋房里,却总喜欢到老城去逛逛。”22岁那年,他借了一个廉价相机,从家里拿一个高腿儿的木凳绑在自行车后架上,天天往老城跑,看各种带砖雕的老房子,甚至“野心勃勃”地想把年画、剪纸、木雕、灯笼、风筝、泥人等天津代表性的民间美术,都做一次田野普查。
在《指指点点说津门》中,冯骥才写道:“评说一个地方,最好的位置是站在门槛上,一只脚踏在里边,一只脚踏在外边。”作为祖籍宁波的天津人,他站在租界看老城,反而更能体会到天津人骨子里的那股劲儿。
03、抢救老街
上世纪90年代,冯骥才开始写作“俗世奇人”系列,每篇写一位市井奇人:“刷子李”刷浆时必须穿一身黑,干完活身上绝没有一个白点儿;“蓝眼”看真假画时,无论尺寸大小,只看半尺,绝不多看一寸;“泥人张”从鞋底抠下一块泥巴,就能捏出活灵活现的人像;“大回”钓鱼,想要哪种就能钓哪种,大的比他还沉,小的比鱼钩还小……他们或富贵或穷顿,却都血气刚烈,幽默戏谑。其间穿插着天津卫的历史地理、节庆吃穿、民艺掌故,于旧日风物中寄托眷恋和感叹。
当冯骥才在小说中再现旧日津门的“俗世奇人”时,现实中的天津老城,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城市改造。
1994年底,大年迫近,冯骥才由媒体上得知,天津老城将被彻底拆除,由香港开发商改造成一座“龙城”——“纯粹香港风情,让人忘了身处天津”。
在轰轰烈烈的城市改造运动中,老城的消逝已成定局,唯一能做的是记录下它的“遗容”。冯骥才组织起一支几十人的“杂牌军”,开始了“抢救老城”的行动,一边寻访历史遗迹,一边将所见所闻拍摄记录下来。
1995年除夕之夜,冯骥才请一位摄影家爬到西北角天津大酒店11层的楼顶,在寒风里拍下天津老城最后一个除夕子午交时、万炮升空的景象。他看到照片,几乎落泪。老城的生命就此定格,成为过往不复的历史画面。
在这场历时一年半的“老城抢救”中,买胶卷、照片冲洗、车费、工作餐费,一切都靠冯骥才卖画筹钱。有时憋屈,也骂街,“当时我说,我像堂·吉诃德,跟一个看不见的巨大风轮作战;我像武训办学,得到处求爷爷告奶奶”。
这些照片后来集结出版,名为《旧城遗韵》,只印了1000部。油墨香味尚未散尽,老城已是断壁残垣。推土机的轰鸣中,古屋老宅被夷为平地,古董贩子们闻风而至,手中拿着那本《旧城遗韵》按图索骥,在积淀了近600年的老城里翻箱倒柜,挑拣残留的历史遗物。
在《挽住我的老城》中,冯骥才写道:“海张五那大宅子呢?明代的文井呢?益德王家那座拱形的刻砖门楼呢?答话的人倒是省事,只说三个字:全没了!谁弄走了?文管部门?房管部门?房主还是贩子们?难道被民工们的大锤全砸了?答话更是省事,还是三个字:谁知道!在一种强烈的虚无感和失落感中,我还感到历史文化出现了一片迷茫与空白。人类在自己的‘进步’面前真是无奈。”
“无奈”还在延续。1999年12月,津门最古老的商业街估衣街即将拆除。拆迁布告如最后通牒,咄咄逼人。像5年前组织抢救老城一样,冯骥才又开始了抢救老街的行动,一面组织团队挨门逐户拍摄照片,用录音机记录下原住民对估衣街的生活回忆;一面与地产开发商、政府官员各色人等周旋,呼吁、撰文、接受采访。
700年一直活着的估衣街,最终还是干干净净地拆了。等冯骥才从巴黎赶回天津,估衣街已被荡为平地,山西商会、青云客栈,还有“五四运动”时学生领袖马骏以头撞柱的天津总商会,全都无影无踪,只剩老字号谦祥益的一个门脸,孤零零地立在废墟上。
“我站在废墟上,真哭呵。我的助手跟了我那么多年,从没见我这么哭过。”几天后,《北京青年报》刊出一整版的长篇报道,题目是《冯骥才哭老街》——这是20世纪末,冯骥才最真实的境遇和心态。

△“抢救老街”最终以失败告终,冯骥才站在已成为废墟的青云栈前。摄于2000年。
04、将书桌搬到田野
在新近出版的《漩涡里》一书中,这一场世纪末的“天津城保卫战”,被冯骥才描述为“一步步走近漩涡”。书中呈现的是一部个人的“文化遗产保护史”,其间掺杂的是文明转型中的忧患、焦灼与困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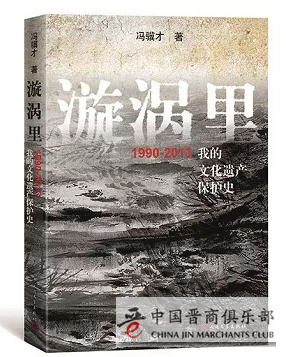
△冯骥才的非虚构作品《漩涡里》。
2001年,冯骥才当选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这一年,他去几个地方跑了一趟,才知道民间文化已是满目疮痍:河北白沟成为小商品集散地,几乎找不到一件他儿时为之着迷的泥玩具。在杨柳青著名的画乡沙窝走街串巷,也找不到一点与年画相关的踪迹。北京吕家营的古玩市场里,各式各样的民间遗存被小贩们堆在库房,任凭寓居北京的外国人选购。有一次,他和一位比利时人争买一辆枣木轿车,一狠心,花掉了一本书的稿费。

△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中,有一座“跳龙门”乡土艺术博物馆,其中藏品来自冯骥才和友人们的珍藏。图为唐代彩绘天王俑。
在大多数中国人告老还乡的年纪,他却越来越忙。2002年,冯骥才60岁,在他的倡议下,“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开始启动,“大到村落,小到荷包”,对“中华大地960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的一切文化进行盘清家底的抢救”。此后10年,他将书桌搬到田野,从年画、剪纸、雕塑到唐卡、羌文化、口头文学,力争将千头万绪的文化脉络全部理清。
龙头项目的年画普查由他亲手来抓。10年里,从滩头高腊梅作坊到凤翔邰立平的画屋,从周庄的纸马店到潍坊杨洛书的同顺堂,从杨柳青的南乡到高密的北乡,他走遍了南北的画乡。人才短缺,调查没人做,他就亲自上阵去做“田野”;档案文字水平参差,他就亲自编辑加工,甚至重写。“他们说,冯骥才你离开文学了。我说我没离开。我对待民间文化,和专家、学者不一样。专家凭着知识,学者凭着思想,我是凭着作家的情怀。”

△图为清末民初《福寿三多》《百事如意》対幅。
最初的“抢救”,一缺红头文件,二缺经费。没有“名分”,冯骥才就四处演讲,上到人民大会堂,面对一屋子委员、部长和司长,一讲两个钟头,说得口干舌燥一身汗,“一定要把他们都感动了”;下到村头破草房,乡长、村长忙着和他留影、吃饭,他就在饭桌上说个不停,“最后他们说,冯骥才,你什么都没吃,你光说了”。
没有经费,他就四处卖画,手腕上都画出一个大疙瘩,得了腱鞘炎。这些画被一批批卖出,最后一次是在苏州博物馆,一屋子的画,卖了358万。
“冯骥才卖画能保护中华文化吗?实际上屁事不管。我卖画,是给自己鼓气、壮胆。”
2012年,70岁的冯骥才又开始了传统村落的保护之路。在过去,他面对的是文化遗存在推土机的轰鸣中被摧毁;如今,新的麻烦与困惑又将他笼罩——一个老村子一旦被列入保护名录,资本与开发商就会蜂拥而上,“腾笼换鸟”,迁走原住民,将其改造为各类商铺、旅店、农家乐、咖啡屋混成一团的“游客的天堂”。
市场化高歌猛进,全球化来势凶猛,纵入时代漩涡20年的冯骥才,是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
他罕见地停顿了五六秒,“应该在这个矛盾之间吧”。遇到在田野与古村做调研的年轻人,他就特别乐观,像发现宝贝一样。但有时又觉得在这个时代,真心、纯粹、无功利的人太少了。“要激活文化,不能完全离开市场。但当文化与市场整合为一,文化本身的精神与价值一定慢慢消损。灯节的时候,各地都表演民俗。在古代,这些民俗寄寓了先民对美好生活的祈望,现在表演的人为了什么呢?我们把所有的节日都变成了娱乐活动,然后再把它商业化,从观念到做法,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链条。”冯骥才说,“这个时候,我又特别悲观。”
如巨树的“大冯”已经77岁了,眼袋越来越深,头上也添了灰白。年轻时画画,他多用黑白,如今却偏爱浓烈的色彩。2013年,朋友送来一种日本制作的金粉,他画了一幅《秋天的颜色》,将金粉混入色彩,纵横涂抹,果然秋色灿烂夺目,意境也焕然一新。
人生的意境也有了变化。这两年,他下田野的时间少了,在书斋里的时间多了,于是重新拾起写作。但对文化遗产与民间艺术,依然心之念之。“我说过,我不会放弃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这不是一句话,是一种思想,是历史责任。”
“就像我掉进这个漩涡里,爬不出来了。”